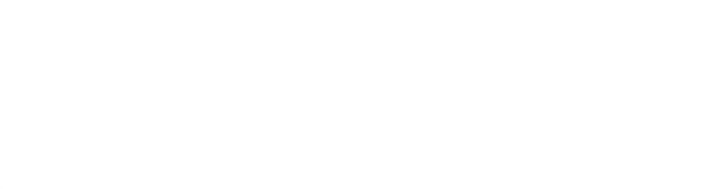- 首页
-
产品中心

产品详情
2007年8月27日,《科学时报》报道:《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前期研究》结题。这项研究立足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概念“主体功能区域”。这个概念将全部国土分成4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在《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前期研究》中,对国土规划提出了3个具体目标:
1.构建高效、节约型、疏密有致的国土利用格局。这着眼于国土开发强度;
2.建设“绿色”、安全的国土,构建国土生态安全屏障。这着眼于整体生态约束;
3.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国土格局,提高国际竞争力。这着眼于经济目标。
看来,在研究者心中有一个“约束最优化”问题:在生态约束的条件下,安排各地区开发强度,以达到整体最优的经济目标。意识到国土的不一样的区域只能承受不同的开发强度,意识到在GDP的赛场上搞“区域竞争”,将导致生态灾难和社会分裂,这些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为获得这个进步,社会已付出了沉重代价。
如果将整个中华大地视为13亿人口的“家”,国土总体设计事关“家计”,为此,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家底”;如果将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视为不同的“物种”,我们应该摸清它们各自适应的“生态龛”。而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形态、色彩的“家底”或“生态龛”,如,降水、流域、耕地、植被、作物、积温、地形、地矿、工业基础、文化积累每个角度都是一个深邃的学科,都能得出有价值的见解。但对国土总体设计而言,哪一个角度才能总揽全局、提纲挈领?
国土总体设计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是全体国民的生存与发展;国土总体设计的基础应该是稳定的,不会在历史演化的长河中随波逐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视角是什么?
《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各省区的人口数据,可据此观察人口的地域分布。然而,以省区为单位太过粗疏。比较理想的数据单位是县。但获取县一级的数据,并将其输入计算机,是笔者没办法完成的工作。
1982年以来,我国推行市管县体制,在大多数省份,各地级市瓜分了全部国土,《城市统计年鉴2005》以地级市为单位提供了2004年的统计数据。地级以上的城市共计287个,输入这个量级的数据,笔者尚可为之,至于一些省区未被地级市囊括的国土,多是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可将其处理为一个单元“其他”。
由此计算出2004年中国人口在国土上的分布情况。多个方面数据显示:50.47%的人口聚集在10.37%的国土上。按聚集人口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广东、四川、安徽、浙江、湖北省内。另外就是各地的人口密集城市,如4个直辖市,一些省会或人口聚集的城市,如西安、衡阳、沈阳、泉州、长沙、福州、大连
70.26%的人口聚集在18.83%的国土上。另外52.15%的国土上只居住了3.1%的人口。按人口稀疏程度,这些国土全部顺次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黑龙江(西北部)、四川(西部)等省区。
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这聚集了50.47%的人口的10.37%的国土,就扮演了“主卧室”的功能,而只居住了3.1%人口的52.15%的国土,显然不适合住人,其功能应在别的方面,需要认真规划。
卓莉等人利用夜间灯光平均强度遥感数据,将县域人口统计数据分布到1×1km
网格上,得出1998年人口密度模拟图(见图一)。(卓莉等《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人口密度模拟》《地理学报》60卷2期,2005年3月)
这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卧室”分布现状。其实,这一格局早在1935年就被发现了。那年,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胡焕庸教授发表了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等值线图。在图上,胡焕庸从爱珲(今黑河)到腾冲画了一条直线,将中国分为东南、西北两半壁,东南集中了96%的人口,而西北仅4%,此即地理学界著名的“胡焕庸线”(见图二)。比较图一与图二发现,经过大半个世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依旧,“胡焕庸线”稳如磐石。
如此稳定的人口分布,其根源何在?“胡焕庸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学者们从气候、降水、植被、灾害、地形甚至长城等许多方面寻找原因,每种原因都能在一定区段内与“胡焕庸线”吻合,但在另外的区段却失效了。
在王静爱的《中国地理》课件中,有一幅农牧交错地带图(见图三),图中可见,中国的农牧交错地带与“胡焕庸线”在很长的区间内吻合。更有趣的是,这个地带是众多江河的水源地。
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则是一条玉米种植带(见图四)。玉米不是我们的原生作物,是明清之际从南美洲引进的。由于其高产、耐贫瘠,使可耕种的土地大为扩张。从有人口记录的战国时期算起,直到18世纪初,1亿人始终是我们的人口上限,每当人口超过甚至仅仅接近这一上限,总会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人口锐减。清雍正年间,中国人口突破了这一上限,究其原因,不少学者归之于玉米、薯类的引入。“胡焕庸线”与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高度吻合,这似乎在提示我们,“胡焕庸线”是耐贫瘠作物的生存边界。
进一步还不难发现,中国的贫穷的地方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见图五)。这暗示我们,在“胡焕庸线”的两侧,资源相对于人口严重不足。
农牧交错区、江河水源区、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缘、贫穷的地方,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问题却被“胡焕庸线”联系在一起。它提示我们,“胡焕庸线”两侧,存在一个意义独特的区域。贫困的人群艰难地生存在这农牧混杂、生态脆弱的区域内,而这个区域的生态变化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这个地区从东北到西南,包括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西北部、山西、陕西、甘肃东部、四川(青藏高原以东地区)、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历史上,这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间征战的主战场;白莲教、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发动的起义,也发生于这个区域;近代史上,红军也是进入这一区域后,才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后方。这个地区的事变往往震撼全国,甚至改变历史的走向。
在这个地区的两侧,东南方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西北方则人烟稀少、生存环境严酷。这个地区搞好了,是东南地区的生态屏障乃至社会屏障;搞糟了,则是整个国家的乱源所在。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了另一个意义下的“东、中、西”格局,它基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在近一个世纪的剧烈社会变动中保持着自己的稳定性。打一个粗略的比方,对社会经济活动而言,这“东、中、西”部不是依行政意志划定的区域,而是3个迥然不同的“生态龛”。这是区域规划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中、西”部的术语。
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经济活动在区域间的分布必然存在巨大差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70.12%的地区生产总值,聚集在10.06%的国土上。按聚集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多少,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江苏(全境)、山东(除菏泽)、广东(含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丽水)、河北(除邢台、张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辽宁(含大连、沈阳、鞍山、盘锦、辽阳)、福建(含厦门、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阳、自贡、内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经济密集城市,如4个直辖市及武汉、长春、大庆、长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阳等省会或经济活动聚集的城市。
其中,除了四川盆地和重庆、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属于“东部”。而在“东部”之内,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诸省。这里我们正真看到,在每个大区内,存在复杂的内部结构。
另一方面,在高达60.23%的国土上,仅有3.07%的地区生产总值。这些国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涉及黑龙江、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
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我们能看到更为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态势。将各地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低到高排列,再计算其与全国均值的偏差,以此为纵坐标,横坐标则取累计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图六。
数据显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区,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这些地区包括京、津、沪和广州、浙江、江苏、山东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厦门、辽宁的大连,一个钢铁城市包头,两个石油城市大庆和克拉玛依。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东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而绝大多数国民所在地,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中等水准。注意,计算图六的曲线时,并未涉及地区内部的差异,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区域间的经济实力差异。这种差异与人口分布差异相关,但比之更极端:越是靠近东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产能力越高。
建国50多年来,对区域发展的策略,一直存在着“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之争,各地方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过这场争论。客观自然环境的巨大差异,最终使“均衡发展”让位于“梯度发展”。然而,20多年的“梯度发展”战略,导致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国民在经济上处于极端弱势地位。
问题的症结何在?“均衡发展”与“梯度发展”,其视角都是经济“发展”,面对“东、中、西”部的国土格局,这样的视角合理吗?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从粮食的视角,我们能看到另一种区域间关系。
如果不计港、澳、台,我们的陆地国土面积为968.8万平方公里。取有关数据得到的2005年粮食产出分布状况显示:在10.6%的国土上(含江苏、河南、山东、安徽、上海、重庆、河北、吉林),产出了42.13%的粮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辽宁、江西、浙江、广东、四川,共计25.99%的国土产出了70.88%的粮食。这些省市分布在4个大区内:黄淮海(28.60%)、湖广(12.91%)、长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东北(8.94%)。可见,约1/4的国土是我们的主粮仓。“无粮不稳”,保障这一些地方粮食的持续稳产,是保障国家安定的基础。区域功能规划,应思考这个问题。
而从粮食余缺的角度,我们能看到另一幅格局(见图七)。先计算各地人均粮食产出与全国均值之差,再从低到高排序,由此得出图七的纵坐标。横坐标则为累计的人口比例。图中曲线与横轴间的面积,则表征着各地粮食的余缺程度。
图七提示我们,人均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全国中等水准的地区顺次为: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河南、新疆、安徽、山东、湖南。而其中有能力大规模向外输出粮食的只有: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这4个省区的粮食产能,决定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机动能力和回旋余地。
人均粮食产量明显低于全国中等水准的地区顺次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青海、海南、福建、陕西。考虑到人口规模和人均缺粮程度,需要大量输入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海南、福建,全都分布在东部沿海,除了海南,正好是东部沿海GDP高度密集的地区。没有了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大量输入的粮食,这里的GDP就无以为继。
其他的地区则基本上可以自给,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历来被视为粮仓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华北平原,虽然产粮比重在各地区中名列前茅(四川名列第三、江苏第五、河北第八),但由于人口密集,只能大体保障自给,已无力大规模输出粮食。
“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川粮外运”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从粮食净输出的角度看,我国已不再是“南粮北调”,而是“北粮南运”。粮食生产呈现出基本自给、净输出、净输入3类区域,这显然是区域功能规划一定要考虑的要素之一。
在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强度高的地区,土地用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压力,推动耕地转化为建设、居住用地。国土资源部现在正竭力防守18亿亩耕地“底线”;而问题的重点是,从全国范围看,应着重考虑的是耕地与建设、居住用地如何规划,而非在所有地方一刀切地防守“底线”。
比如,海河流域,从明、清时代起就是靠“南粮北运”平衡粮食供需,而今河北平原成了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海河流域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其后果却是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占到流域总用水量的1/3,而海河流域的用水量,农业灌溉占到了七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格局。
工业是现代化的基础。工业的分布则展示出不同于粮食的格局,提出了另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数据显示:在10.7%的国土上聚集了84.34%的工业生产能力,这些国土主要顺次分布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福建、北京。全在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
2005年,出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93.6%;进口商品金额中,工业制成品占77.6%。由此,我们大家可以通过比较各地区进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的关系,来分析各地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见图九)。
数据显示:最发达的沿海工业地区(包括广东、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苏、浙江),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海外而非为自己的国家生产消费品与生产资料。而出口比重低于10%,主要为国内生产的地区,大多是工业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江苏、海南等沿海地区,进口占了很大比重;而绝大多数内陆地区,进口低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10%。
从工业的角度,国土事实上被分为两个部分:狭长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主要的工业生产能力,并且对海外的联系和依赖远高于对内地的联系和依赖;而广大内陆地区,相对而言工业极不发达,同时,与海外的经济关系薄弱。
这种态势,是20多年“政策倾斜”、“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的必然后果。它彰显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地理分布:一个狭长而严重依赖海外的沿海工业带,和工业落后、相对封闭的广大内陆地区并存。
从分工角度看,工业集中分布并不是严重问题,然而,工业集中区与国家别的地方的关系则必须认认真真地对待。如果工业集中区热衷于充当“世界工厂”,无制约地消耗国内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利用自己在GDP中的优势地位挟持公共事务决策,谋取政策优势,而对广大内陆的生态破坏和经济凋敝无动于衷;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国民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方面差异巨大,在价值标准、思维方法方面无法沟通,势必危及国家的统一。
至此,我们正真看到,自然禀赋与经济活动在地域上存在着各种鲜明的分布格局。顺理成章,各地区本应相互协同、各司其职,建设好我们这个“家”。然而,20多年来,我们正真看到的却是“区域间经济竞争”。
自1980年开始慢慢地推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以来,各级地方政府成了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对它们而言,自己的“发展”立刻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硬道理”。在我国,各级政府在当地拥有绝大多数经济资源和几乎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当各级政府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后,它们相互间迅速形成了竞争关系。
20多年来,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居然造成一种“学术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2007年3月1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表了《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
“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之间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综合竞争力。”
这项研究,用国家间经济竞争的理论来指导国内各级地方政府,而国家间竞争的大背景是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无政府主义国际秩序!国家间经济竞争的主流理论,其基本出发点是:站在人格化资本的立场上,评估资本盈利的社会环境,为资本选择盈利的载体。
这所谓的“竞争力”最后归结为对资本的吸引力,于是各地方政府不厌其烦地宣示:“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卷入了一场吸引资本的竞争之中。各地方间的关系被隐然视为相互竞争的国家间关系。
山西长治,以“三零政策”(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外地客商,结果却被卷入了一场闽商与本地富豪间的争斗中。当地政府、党委、纪委、法院、人大无一能置身事外(见王中宇《当今“上党战役”》,《科学时报》2007年9月17日 第八版)。人们固然可以批评当地有关方面不讲原则、违法乱纪,然而导致这“三零政策”的根源何在?经济实力上与东部的巨大差距、现实的财政压力和“赶超”的迫切愿望无疑是最直接的动因。
重庆南川市的金佛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体量仅次于三峡景区,以原始珍稀森林为主要特征,为全球同纬度地区两个硕果仅存的原始绿阔叶地带之一,动植物种类丰富。植物包括银杉、珙桐群落、杜鹃王、古银杏、方竹、大叶茶;动物包括华南虎、金钱豹、云豹、白颊黑叶猴、灰金丝猴、猕猴、大灵猫、小灵猫、红腹锦鸡、穿山甲、水獭等。
然而,这里的经济严重依赖于采煤。由于金佛山体主要由铝矾土构成,当地对开发铝矾土寄以巨大期望。有报道称:
“在南川市的大力扶持下,博赛矿业公司很快达到了年产5万吨铝矾土的规模。2001年12月,博赛矿业投资2.5亿元,开工建设年产7万吨的氧化铝一期工程,2003年9月南川市氧化铝厂竣工投产,成为全国第一家生产氧化铝的非公有制企业,结束了川渝两地无氧化铝生产的历史。目前,博赛矿业已达到年产棕刚玉13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棕刚玉生产企业。”
“从2001年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以来,南川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原煤机焦化工耐火黏土建材火电产业工业链。”
其实,早在2000年6月,国家机械工业局公布20种机械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其中就有“棕刚玉、绿碳化硅、黑碳化硅等烧结块及磨料生产能力过剩”。
南川努力打造的产业链,无疑对当地生态形成巨大威胁。增加过剩产品的产能,从全局看,只能增加出口压力。结果以破坏自己的生态、消耗紧缺的能源为代价,为外国提供他们不愿生产的产品。
站在全局的角度,在南川搞“工业强市”无疑是不可取的。然而,不搞工业,何来税收?当地仅教师工资,就对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保护金佛山,获益者是重庆、贵州、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国家,而代价却压在当地百姓与政府身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爆发了几轮区域经济冲突。1980年前后,各地在轻纺产品和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行业进行了大量的重复建设;1985至1988年,重复建设发生于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领域;1992年以后,重复建设的领域大多分布在在汽车、电子、机械、石化等重化工业。2002年后重复建设爆发于钢铁厂、电解铝、发电厂领域。南川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大规模开发铝矾土的。
一再爆发的重复建设,导致各地大范围的产业体系雷同,一次次造成全行业的恶性竞争,导致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资源破坏,令经济学家们头疼不已。有无数的论文痛陈重复建设、产业体系雷同的危害,有无数的文件指责地方政府不顾大局。然而,在“区域间竞争”的大环境下,哪个地方不在当时最能来钱的方向上投入竞争,并赢得胜利,哪个地方就只能被边缘化。
没有人愿意贫,没有人愿意被人嫌,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而局部的经济理性却导致了全局的非理性。
这“区域间经济竞争”的遗害之深,几乎无微不至。“搞钱”替代“政治”占到了“一元化领导”的位置上,而分工、协同则被漠然视之。某些地方政府,大搞“全员引资”,将招商引资的指标分解到每一位干部身上,也不管他分管的是政法、文教还是纪检。有的企业则搞“全员销售”,不管他是在研发部门还是在生产部门。笔者的一位同学,曾在某研究所当所长,他们的政策是“各自出去啄米吃”,让研究人员自谋经费,而这个研究所的专业居然是“历史”!
无怪乎有民谣云:“新生活,各顾各。”人们似乎淡忘了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在一个世纪里沦为“一盘散沙”的历史。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的英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忧虑道:
“我国许多省份很有自己的特殊性。有的省经济实力很强大,有的省(区)资源储备巨大,有的省人口众多,还有的省(区)辖区面积广阔,更有的省(区)则有民族特殊性。从长远看,这种特殊性或不平衡性并不能构成一些省(区)裂土分离的条件。但不排除特定时期,某些政治家可能利用特定的区域资源而采用激进的政治立场,提出过分自治乃至更极端的政治要求。”(
GDP高的地区自然认为,别人离不开它,只有它嫌别人的份儿。这一些地方的官员喜欢列举本地在GDP和财政收入方面所占的比重。中部那些贫穷的地方似乎也认同这一点,于是拼命地、不择手段地要将本地的GDP搞大。一个长期统治各级政府的潜意识是:除了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各地区没有质的差异,大家是各自独立的竞争者,只能在GDP的赛场上竞争,优胜劣汰、赢家通吃。
站在华北,京津冀无疑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然而这个地区要能持续生存下去,水资源的良性循环至关重要。燕山、太行山的植被与生态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京津冀地区的水资源状况。为保障京津冀地区的持续生存,势必限制燕山、太行山的经济开发,这将涉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西部、山西东部的定位与发展。一个在全局上合理的定位,将使这个地区在GDP的竞争中一直处在弱势,甚至需要长期的大量投入而看不到资金回报。
始建于1958年的岗南水库是滹沱河上游最大的水库,它是石家庄市的主要水源地。为保障2008年北京奥运会,据称,即使未来两年干旱,岗南水库也一定要保证向北京供应足量的水源。(《新京报》2006.8.22)。
上个世纪60年代,岗南水库年均入库水量为14.25亿立方米,进入本世纪后降为3亿立方米。在岗南水库的上游,山西省正在申报建设忻州市定襄县坪上水库,它是解决忻定盆地缺水的关键性工程,计划年供水量1.31亿立方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旦这个水库建成,岗南水库这区区3亿立方米的入库量至少要砍掉一半,石家庄怎么办?北京怎么办?不让建?坪上水库要解决的是忻定盆地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
由此,我们正真看到的,不是这些地区离不开京津冀,而是京津冀依赖这个地区而生存。说白了,京津冀与这个地区是一个整体海河流域。在海河流域里,经济发达地区与生态屏障地区是相互依存关系,绝非相互竞争关系。恰如在一个家里,厨房与后花园各有分工,谈不上竞争。你之所以能大把挣钱,是别的地区的同胞为你作出了牺牲。
由此,京津冀对燕山、太行山地区的生态保护,对这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绝非“发扬风格”、“救助”、“施舍”,这是京津冀自身长治久安所必须。而以邻为壑,自顾自地搞“区域间竞争”,无视“环京津贫困带”的困境,等于自杀。
布衣学者杨勇1988年徒步考察了金沙江,随即给当时的领导人写信,反映金沙江灾害威胁严重,对下游有危险,并建议停止开采森林。然而金沙江流域的伐木一直持续到10年后的长江大洪水。这场洪水给长江中下游造成了1800亿元的损失。有人计算过:
“国营森工企业在迪庆采伐木材近30年,加上群众的自用材以及偷砍的木材,年均采伐木材140万立方米,采走木材3000万立方米。以10元一方计算,合3亿元以上;以100元一方计算,合30亿元以上。”(刘建华《中甸遐想》,《迪庆日报》2007.1.12)
30亿对1800亿,这账傻瓜也能算明白。如果长江中下游用1800亿元的10%来帮助金沙江流域的产业转型和生态保护,明显是个双赢的局面。这180亿元如果按中下游各省经济实力分摊,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在“区域间经济竞争”的大环境下,长三角忙于“做大做强”,中游忙于“对接”、“赶超”,上游则陷于为生计而战。直到10年之后的大洪水,才让中下游明白:上游的生态环境决定着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共生、分工、协同远重于竞争。GDP高的地区,不过是分工侧重搞经济;而分工侧重于环保的地区,不但不应加入GDP的竞争,而且需要大量而持续的、没有金钱回报的生态投入,这投入的来源只能是那些GDP高的地区,这不是“发扬风格”,而是为了它们自己的持续生存。
这个道理似乎日本人比我们更明白。就在我们热衷于“区域间经济竞争”时,1998年,日本人成立了一个世界沙漠绿化协会,帮助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治理生态环境,自2000年至今,他们已先后9次到阿拉善植树。另据新华网2007年8月6日报道:“日本将无偿对华援助约8700万元人民币,与中方合作,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开展治沙造林项目。”
我们的各个地区、各级政府何时才能真正明白共生、分工与协同的道理,并将自己的功能定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个造成“区域间经济竞争”的财政“分灶吃饭”体制,是否该反思了?我们是不是该警惕,中华民族被外来的洋教条和内部的理性经济人重新消解为“一盘散沙”?何时,我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能落实到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政治经济行动中,不再停留在歌词上?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伴随她。”《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