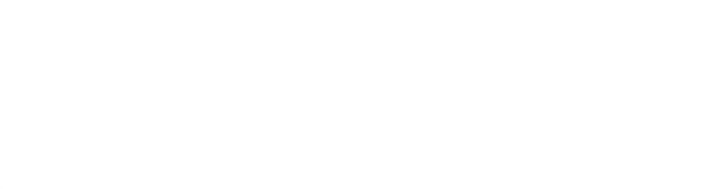- 首页
-
产品中心

产品详情
1923年初,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因清华学生而起。胡适为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开出引起争议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梁启超认为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不符合清华学生的特定要求。这次“国学书目”之争成为1923-1924 年间就整理国故问题引发的整合观念大讨论的导火索。这场论争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一起进行,互为表里,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复杂态度和思考。
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始于1923 年初,大约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同时,而且与后者一样是因清华学生而起。不知是由于即将出国的清华学生特别想从当时思想界领袖人物那里寻求出国前的最后指点,还是这些思想领袖受五四影响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清华的学生,或者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总之清华学生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连续扮演了两次思想论争导火索的角色。
1923 年3 月,胡适应几位将赴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的请求,开出了一份后来引起争议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自己解释说,提出要求的清华学生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开出的书目虽然主要仅涉及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领域,程度却并不低,数量也非常大,既不能说是“最低限度”,也绝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读完。
梁启超当时就指责胡适开的书目“文不对题”,不符合清华学生的特定要求。他认为胡适不过将自己正在做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写出来(按梁这个推测大致可成立),“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实际上,许多书更是“做白话文学史”的人才需要读的,不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
他感到“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早年甚为推崇小说的梁氏自己坦承并未读过这两部小说,但若因此“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他“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后来裘匡庐也攻击胡适说,“修习国学,必以诵读古书为本”。但胡适的国学书目,“ 标曰‘ 最低限度’, 而所列之书, 广博无限[垠?]。……论其数量,则已逾万卷;论其类别,则昔人所谓专门之学者,亦已逾十门”。裘氏亦留学生,但他对中国学术的分类仍依旧义,显然不像梁、胡那样接受西来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分类。就传统的学术分类看,“自汉唐以来,未闻有一人而兼经学、小学、性理、考据、佛典、词章、词曲之长者”。实际上,“古来宏博之士,能深通其一门者,已为翘然杰出之材;若能兼通数门,则一代数百年中,不过数人;若谓综上所列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这样一些“古今鸿儒硕士所万不能兼通者,某先生乃欲令中学学生兼习之,又复标其名曰‘最低限度’;吾不解某先生所谓高等者,其课程复将奚若?”。
所以他的结论是:“凡自谓于学无所不通,此仅可欺浅学无识之辈,若通儒则决无此论”。而“今日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无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则享名亦愈盛”。像这样“欺人之甚,而言者悍然不惭,闻者茫然莫辨”,说明当时“世人既多妄人,复多愚人;非妄人无以益愚人之愚,非愚人无以长妄人之妄”。这种“夸而不实、高而不切”的做法是今昔文人的通病,体现出其“欺世之意多而利人之心少、自炫之意多而作育之心少”。
按胡适所开书目确不能说没有一点“自炫”之心,鲁迅约十年后说到他自己因多翻书而看似博雅时,也婉转讽刺说,“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胡适开书目那一段时间与周氏兄弟学术过从较密,时常相互借书,所以鲁迅对胡适读书的范围大致是了解的。从胡适早年读书的有关的资料看,书目中有些书的确可能是他觉得应读而自己尚未读的,至少是他留学之前没有读过的。但其一生注重方法,以为掌握了“科学方法”后便可一通百通(实际是否如此当别论),也是实情。所以对胡适来说,具体读书量的多少恐怕是次要的,重点是读者是否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其实他要在读书数量上“自炫”正因其对旧文献的自信尚不十分足,他若真敢于“欺世”,其所恃也正在“方法”之上)。
裘匡庐认识到,对追随书目而读书的青年重要的是,若其对上述欺人之言“不察而深信之,始则扞格不入,继则望洋生叹,终亦必至甘于自暴自弃而已”。这一后果当然非开书目者之所欲观,而胡适的书目也确实不能免除这方面的指责。虽然他在书目中不列基本的史书,却又开出了崔适的《史记探原》、崔述的《考信录》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很可能是受钱玄同影响)。梁启超就此提出了疑问:在“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怎么能读这些书呢?“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原》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
《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因此写信给胡适,一方面指责他违背了自己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所说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的广泛定义,将“国学”的范围缩小为“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胡适又“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的真实的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必须要知道”的书目,使其读了这些书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胡适复信婉转承认《清华周刊》的记者所论不误,并开出一份仅约40种书的“真是不可少的”书目。
大约同时,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其数量也不少。不过他同时又开具一份“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仅收书约25 种。梁氏以为这些书是工科学生也必须读的,“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在他看来,“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后者尤其是见道之解,梁氏以不断转换观念“与昔日之我战”而著称于世,而与社会“共同意识”保持“一致”很可能即是他的考虑之一。梁启超自己当年曾是主张“开民智”者,这大约也是在生活经验中悟得的教训。那些仍在主张“启蒙”的新人却尚未能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走近大众的同时往往又疏离于大众。
时在清华学校任职的张彭春看了胡适的“国学书目”后,感觉“从这个书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国学的法门”,倒是“能够准确的看出胡先生所谓国学的是从这些书中得来的”。他认为,“把这些书按胡先生的次序从头到尾读一遍”即是胡适提倡的“历史的国学研究法”,不过这更是一种可试行于大学国学科专心研究思想史同文学史的少数人的“死工夫”。至于“为大多数教育的问题”,即“那些不能专心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这方面,胡适并未提供答案。张彭春与其他人一样看到了书目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他自己读了这一书目后立刻也想尝试一下国学研究,充足表现了这一书目的影响。的确,当时甚享时誉的梁、胡二人皆开具“国学书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虽然二人的出发点和立意不同,读者对书目的接收和反应也各异,这个象征性举动的影响仍迅速扩充到全国。
在东北的金毓黻到1923 年7 月才注意到梁启超和胡适所开的国学书目,金氏虽觉二人所开书目皆有不足,却特别肯定“二氏皆新学巨子,胡氏复究心西籍,于举世唾弃之国学,宜不屑言;乃不吝开示,委曲详尽,至于如此,虽老师宿儒,有不能道其仿佛者”。从“举世唾弃之国学”一语看,整理国故的风潮此时基本未波及东北。时人或更多的后之研究者多已视这时的梁启超为落伍,但金毓黻却把握到了问题的实质:就“国学”而言,梁其实与胡适一样是“新学巨子”。由“新学巨子”来开示国学书目的影响非常大,约三个月后,金氏读到其北大同学陈钟凡(斠玄)之国学书目时,已说“近来治国学者铜洛相应,风起云涌,虽其所言或出于稗贩、或缘饰新说,然所获亦不少”。短短几个月间,国学的社会反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渐有席卷天下之势了。再到次年6 月,他又见《东方杂志》载李笠辑《国学用书撰要》,深感“近顷国内名流,喜以研治国学途径开示后学,诚前此所罕见也”。
到1925 年2 月,沈雁冰注意到一本新出的《中国文学源流》,发现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古今诗文选,颇觉“这部书竟是我们从前看见过的胡适之、梁任公诸位先生所发表过的‘国学书目’的‘广注’。可怜中国太穷,中学生或有中学同等程度的中国文学愿研究者,却终于没有钱按图索骥去买那些国学书”,于是有此书之作,“倒不如用了个‘胡梁国学书目广注’的名目”。沈氏陈述的态度虽然是负面的,仍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国学书目”在当时的影响。陈源稍后也注意到,自从胡、梁开出国学书目,“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章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
再稍后,曾经试图为“整理国故”正名但已转而持反对态度的郑振铎指出,“自从某先生开列了他的无所不包的国学书目以后,便大众都来开书目,且竟有人以补正‘国学书目’之故而荣膺大学教授之职的”。结果是所谓“国学”在“经过了好几次的似若‘沦亡’的危境”后“又抬头起来了:所谓国学要籍的宝库,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之类,每个中上等的家庭里,几乎都各有一部;而《古今图书集成》也有了资格和《英国百科全书》一同陈列于某一种‘学贯中西’的先生们的书架上。几种关于‘国学’的小丛书,其流传之盛,更百倍于所谓‘科学小丛书’”。不仅“每一个大学开了门,总有一个所谓‘国学系’”;就是“每一位国学大师也总有他的许多信徒与群众。自《国学书目》开列出来以后,总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郑振铎这样的年轻人是隔了五六年才看出“新学巨子”开示国学书目这一象征性举动的广泛影响,在他眼里“国学书目”此时已转为造成复旧的负面象征。老谋深算的吴稚晖当时即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但他正式的表述却基本只针对梁启超而略过胡适(实际当然同样针对胡适),梁实秋曾对此提出置疑,吴稚晖精确指出,他正有国学书目“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的意思。因为“梁启超一动笔,其福利人与灾祸人,皆非寻常”。因其影响太大,故非反对不可(这实际上也是胡适等人那时要反对梁关于“科学”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实秋或“以为是个党派问题”,吴则承认“我在政治问题上,党派之见很重。我在学问上,还不配我来讲什么党派”。
吴氏反对“新学巨子”来提倡整理国故有着较一般人更深的忧虑,即形成他所谓中西结合的“洋八股”;在西学掌握“话语权势”的时代,若中国传统有西学为之正名,就无法破除打倒了。1923 年10 月,《北京晚报》载范源濂的谈话说:“欧美各国所研究之文学,均着重于本国方面,他国之文学鲜有研究者。今观吾国则不然,所讨论之文学,大都属于欧西,而以前之旧文学,研究者绝少,故罕有得文学上之重大价值者。”
吴稚晖借机攻击梁启超开国学书目说,“我国近来却极留意自己文学,但恐旧国粹气太重,所以载了许多线装书出洋,与别国文字配合起来,如是乃化合为洋八股”,实际上也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新国粹”。梁启超或者以为“破坏时期已过,现在正应建设”,所以开国学书目。吴自己“三年前也以为正应建设,不料瞪开了眼睛看了三年,方觉悟圣经贤传的祸国殃民比未开海禁以前还要利害。若真真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惟梁卓如先生来用力鼓吹,可望成此伟大结果”。
他认为,梁启超本是“推倒旧八股的魁首”,其在戊戌前后所著的《西学书目表》“虽鄙陋得可以,然在精神上批评,要算光焰万丈”。故梁“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把那精神衔之刺骨”。但他近来“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讲演,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既然梁启超已变成新的张之洞,吴不得不“袭他的隔年历本,来唱老调”,所以其批评专为“贡献梁卓如先生”,而不针对后辈。
梁启超在1922 年前后治学取向确有明显的转变,被眼光老辣的吴稚晖一眼看出。在他看来,当时已“降尊在学校里去讲历史”的梁启超若“客观的整理了事实,作一有系统的讲授,非但青年要晓得一些‘中国史之大概’,可不必泛求于许多祸国殃民的老国故,而且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担当”。所以吴氏肯定梁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部要得的书”。但他在紧随其后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论著中提出的“那种主观的政治思想,换言之所谓‘中国人的人生观’,及那种灰色的陈腐书目,终竟要不得”。
梁实秋对吴稚晖斥梁启超所开“国学书目”为“灰色”大为不满,他认为吴“似乎不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反倒是吴自己的文章才有点“灰色”,因为看了不知所云,而“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吴氏有两大误解,一是梁启超本无意“造就一大批整理国故的人才,只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二是梁书目中给留学生带出国的只有十几种,并非全部。其实吴稚晖并不十分在乎梁启超书目的详细的细节内容,他根本反对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让青年来读中国旧书(详后)。
梁实秋本人即是清华毕业的留学生(他1923 年8 月离上海,9 月初抵美国,此文约作于抵美前后),他在这里涉及一个久存于国人心中的问题:中国出洋的留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主持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吴稚晖大概认为他对留学应有充分的发言权,故激烈批判梁启超和胡适为即将出洋的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反对留学生带线装书出洋。他自称“近来思之思之,留学局面,亦可惨伤。即使卑之无甚高论,文凭即算终身大事,然按部就班,扎硬寨、打死仗,得步进步,亦未为失计。吾以为无论上了日本欧美之岸,第一先将外国话说得熟溜,第二再将外国文写得畅达……无此程度而入学,皆挂招牌骗自己耳”。若外文学好,即使辍学回国,“作一外国文教师,亦良教师矣”;较之混一文凭回来“作一世欺人勾当者,似乎远胜”;更比那些“憧憧扰扰,一年迁移数处,群聚而为哄争,思吃天鹅之肉,闹得鸡犬不宁者,自尤远有益也”。
吴的言论引起几位正式读学位的留学新派人物的反弹(这里或者隐存谁对“留学”更有发言权的竞争,但这些人无疑都比吴更了解包括“科学”在内的西学)。胡适的学生罗家伦大致赞同吴稚晖的意见,而林玉堂则和梁实秋一样几乎完全不同意。
先是《清华周刊》的“记者”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对于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言,“国学书目”实际反映了“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他们都以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必也不会太高。其实当时社会对参与文教事业的留学生的确有较高的国学要求,留学归国的张彭春在清华任教务主任,即发现因其国学程度差而常为同事所看不起,故非常羡慕也是留学归国而任职清华的吴宓在旧学方面的修养。
胡适针对清华学生的观点反驳说,“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这是胡适长期持有的观念,他对许多中国留学生不通国学甚至不通中文的情形深感耻辱,而自己留学时就一直在“预备”回国后作“国人导师”。
同样考虑到留学生归国后在中国的影响,梁启超也认为清华学生应该对“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因为他们“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他说,“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而要在中国社会有影响,就一定要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国学修养,否则,“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
不过梁启超说的国学修养是针对留学生的整体治学而言,具体到留学的那一段时间,则他与胡适的看法还很不同。当清华学生问到在美国游学期间应否读中国书时,梁以为在美期间“可以不必读中国书,还是专心做功课好。然而我很劝你们带几部文学的书去,如《楚辞》《文选》等等,在课暇可以拿中国东西来做你的娱乐”。反倒是梁实秋并不认为这些书仅供娱乐之需,而是“一切要学习中国韵文散文者所必备的根基书,没有充分读过这种‘臭东西’的,不要说四六电报打不出,即是白话文也写不明白”。
时在美国的前北大学生罗家伦则表示“根本赞成”吴稚晖反对留学生带线装书出洋的观点,他以为,“留学生在国外,是有限的几年,也是‘天赋的’最好机会。大家总当利用这个很短的几年,以最经济的方法,学只有在国外能学的东西。还不算学问,只是打个基础,回国后有继续研究的希望。把这个打基础的机会失去了,真是可惜。至于学国文的机会,回国以后有的正多。”罗氏指出,“胡、梁二先生的错误,是仿佛的认定留学生的‘专门’都是一样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去教人家从他们。胡先生恐怕忘了他在国外是在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初稿。梁先生恐怕忘了他自己以前国学的根底和他自己在国外是研究中国学问的情形”。
罗家伦这么说有其自身的经历为依据。也许是受老师胡适的影响,他自己“三年前出国的时候,也带了三五百本的‘线装书’”,从《十三经》到章太炎的著作都有。“并不是经人指定,而且有些还是我平常喜欢看的书。但是到美以后,除少数几种为特别目的被参考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放箱子底下不曾翻过。过些时候又要‘完璧归赵’了”。故留学生“苟非到外国来‘保存国粹’,又何必作这种傻子呢?”。
实际上,“如果要在国外做一个好好的大学生,或大学院生,老实说,看与自己研究课目有关系的书,是来不及的。而且语言文字,无论在国内学得如何,到国外来若是想正式研究学问,总是不够的。国立学校的学生或者有些曾经用过蛮力多读过几本外国书,教会学校或‘准’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会多说几句洋泾浜的外国话,但是其不够则一。所以初来的一年半载,还要在文字上费许多工夫。……把这个难关打开,要治一点学问了。于是教授指定、或自己发现所当看的书籍,真是如‘急雨淋头’,一天到晚来不及的。何况自己对于教授所呈的报告和研究集会时所读的论文呢?”。除此以外还有第二、第三外国语的书要读,故实无暇来读线装书。
此时距胡适留学美国已过了约十年,而罗家伦所见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情形与前无大改变,多数“留学生平均读中文书的程度”,一般是“看外国文十叶的时间,看中国文不能到一叶”。这些人大概的困难有三,即掌握的“生字成语太少”、“于文法的构造不明了”也“不曾习惯”。这分明是外国人学中文的感受,可知当时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的确太差。
不过,罗氏的观念其实同梁启超差不多,他并不反对出国者少带一点中国书:“不问他中文有根底或没有根底,老实不客气的劝他只带以下三部书:《十三经白文》(除《诗经》《论语》《孟子》数种可读而外,其余亦不过备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十八家诗钞》。若查考生字,则再带一部《康熙字典》。若是再要学做国语文,则添带《红楼梦》一部、《水浒》一部”。
也许罗家伦已尽可能降低标准,但如果他描绘的留学生中文情形不错,恐怕他所推荐的三部书这些人也没有很好的方法看,可知他的微小书目同样不切实际。这里同时还涉及留学生的自我定位和社会对留学生的期望。胡适是要预备作国人导师的,所以他的确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应付功课;若真要到外国求具体的学问,又欲应付学位方面的要求,则实如罗家伦所说是没多少读闲书的时间。另一方面,如果留学生回国仅在洋行一类机构工作,则其中文是否通顺当无大问题。假如要在中国机构工作甚至还要承担起士人对社会的责任,则胡适和梁启超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罗氏曾举例说,有位留学生从他那里借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个星期还未能看完。“他若是以看这本书的时间去看Bernheim、Shotwell 等关于历史方法的书,岂不是比看梁先生的书所得多了多”?从吸收西学的角度言,此语确不错;但此人若回国教书治学,虽西学精通而不能出其学以飨国人,则于中国何补?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梁启超所说,派遣留学还不如“进口”外国学者。
不过罗家伦所论还有弦外之音,他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好的不过是论中国史料的二章,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至于论历史性质、范围等理论和方法,则“比他国史家著作差得远了”。留学之后对西学已有较深入认识的罗家伦感到“梁先生看外国书的范围和了解程度,实在使我怀疑。我的怀疑或者错误,但是近来看他的几种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实使我增加这种印象。其实梁先生在中国学问方面,自有他的地位,不必有时带出博览西洋群籍的空气。并且有许多地方,若是他公认不曾看过西籍,我们只是佩服它的天才;若是说他看过此类的西籍,则我们不但以另一种眼光批评,而且许多遗误不合,或在西方早已更进一步之处,梁先生至今还以‘瑰宝’视之,则我们反而不免笑梁先生西洋学问之浅薄”。
罗家伦显然希望西学浅薄的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方面努力,梁自己那时也一面继续主张学习西方,一面有意识地想为中国文化正名,故被许多人视为“东方文化派”。问题就在于,梁启超在中国正以“新学”闻名于世,若论“中国独有的”学术,且不说许多纯粹旧派的遗老尚在,便是新旧兼具的章太炎也远在梁氏之上。
吴稚晖就充分承认梁启超在使中国人走向趋新一面的努力,而且认为继续朝此方向前进才是梁的历史地位所赋予他的责任。吴氏指出,“倘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没有梁卓如先生积极的赞助,或梁卓如先生也如章行严先生的忽加非议,简直白话文至今焦头烂额,亦未可定。梁先生于中国有大功二:一是唤醒国人来维新,一是确助白话文成功”。如果他要整理国故,“若由于不能自己藉以消遣,原是无所为而为的为学极规”;然“倘有兼在后世儒林、文苑传中分一席之意,则是有所为而为,未有不谬”。盖“梁先生已是历史上一大人物”,其对于“中国的工作,尚多未竟之志愿。似乎使中国人手里有机关枪,比较能使中国人能做洋八股为要”。
最后一句话反映了吴稚晖及一部分人当时的观念,他们都以为中国人在“文化”路向上已走得太远,应该回归到“物质”的层面;为了这一目的,这些人感到有必要重新诠释“西洋文明”并付诸实践。在学习西方仍是中国的发展目标而因“西方的分裂”使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已渐呈多元化之时,重新为“西方文明”定位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努力方向(“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即是这一努力的一个体现)。不过这一重新界定“西方”的努力又基本是“中国”的,不仅因为其关怀是中国的,更因不少参与这一努力之人的西学知识(像罗家伦眼中的梁启超一样)并不深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下,整理国故成为与西方物质文明关联紧密而又对立的象征,因而也就成为那些重新诠释西洋文明者攻击的对象。
本文节选自《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罗志田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10),原标题为《“国学书目”的争论及其弦外之音》。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全球“滥交”指数榜单公布!澳人数量排第二,中国倒数,榜首出人意料
读书、思考、文化、史学,本号主要推送近现代史领域文、史、哲、政、法等方面优秀文章。
排队3小时,拒签1分钟,80%的留学生都不知道的面签大坑竟然是......
华为 WATCH GT 4 草木绿、华为手环 9 明日预售,4 月 12 日开售